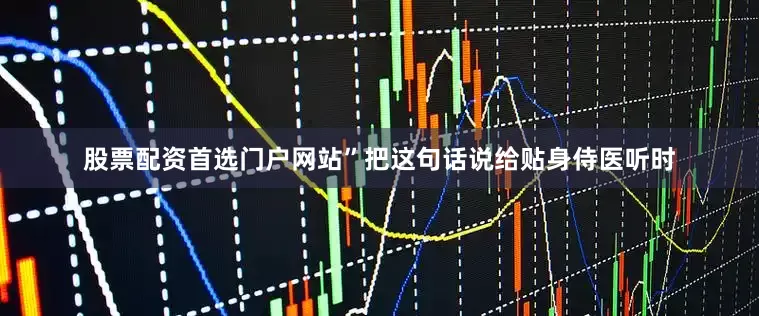
“1959年12月的冷风真刺骨,你们记着,等我咽气那天,院子里不许有人嚎啕。”把这句话说给贴身侍医听时,阳明山的落日只剩一抹残红。对照他那份七条遗嘱,最扎眼的便是第五条——不要放声而哭。熟悉旧军阀礼数的人都明白,丧礼原本讲究排场,哭声越大越显得“忠孝”。阎锡山为何反其道而行?要弄清这点,不得不把时间轴往前拨。

一九四九年春,太原外围炮声隆隆。阎锡山站在座机舷窗旁,远处山西的土黄色大院渐成黑点,心里跟被铁锤砸了一下。这一别,他和晋军三十八年的纠缠到头了。飞抵南京后,他很清楚:枪杆子没了,想在国民党高层继续生存,只能用政治投机补漏洞。于是他既去美国大使馆同司徒雷登寒暄,又在蒋介石与间奔走,前后递了不下十封箴言,摆出“调停者”的身段。对外他自嘲道:“阎某人如今靠嘴吃饭了。”
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时,各路文武百官心知大势已去。“谁来扶这只破船?”这是当时中常会上最尖锐的问题。蒋介石一开始属意嫡系,奈何人才凋零,只得对阎锡山点头示意。阎乘机请假赴台奔丧,实际上是飞去溪口面见老蒋,摆明“唯命是从”。蒋将他推上“行政院长”位置,顺手把一堆烂摊子塞给他:财政见底、军心涣散、外交断线。阎锡山心里门清,这是“临时打火机”,随时会被掐灭。
尽管如此,他还是搞了场银元券改革;在西北扶植马家军;派携带银箱去游说董其武;又和绥西屯垦军接洽,希望能在河套筑一道屏障。用他自己的话讲:“明知无望,也得做个样子。”然而三道防线相继坍塌,广州、重庆、成都的败退节奏像多米诺骨牌。十二月初他仓皇飞台,一路回想,冷汗直冒:原来失去根据地后,自己连半点定价权都没有。

登陆台湾后,阎锡山表面上仍是“行政院长”。可蒋介石很快复职,将他易位。陈诚上台那天,阎只说了四个字:“早料如此。”从此,他与政治中心保持距离,搬进阳明山菁山草庐。那里没有自来水,没有电灯,仅有几间木屋和一孔他亲手设计的窑洞。窑洞被命名为“种能洞”,寓意“种德修能”。有人问他为什么选这种苦地方,他抬头望雾气,“人老了,得留点空间跟自己算总账。”
菁山草庐陆续聚集了五十多名旧部,轮班照顾他的衣食起居。阎氏行事一向精细:鸡蛋必须当天上午捡、午餐米饭必须八分熟、写作间不得有油墨味。可一旦进书房,他能连续伏案十二小时。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记得那盆炭火——冬季手脚冰凉,他把稿纸烘得微卷,再抬笔疾书。

这十年,他完成《中的哲学》《补心录》等数百万字手稿,还断断续续改写《思想日记》。在日记第百段,他写了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功业尽处,剩一个身心学问可守。”这句话后来被他指定刻在墓碑上,也是遗嘱第六条的核心。
一九五八年,老友杨爱源病逝;翌年徐永昌也走了。两场丧礼,阎锡山都带病出席。徐家灵堂外,他对贾景德低声说:“人一个个走,我也差不多。”或许正是好友纷纷谢幕,让他提前预演自己的结局。遗嘱七条全部是细节:联幛、花木、诵读篇章、出殡时间,条条看似鸡毛蒜皮,却透露“节俭”“宁静”四字。最特别的是第五条“不要放声而哭”。倘若放大镜细察,他的考量可以归纳为三点:
其一,对权力游戏彻底绝望。他曾在阜新机场某次闲谈,说过一句类似牢骚的话:“哭得震天响,于亡者无补,于生者是演戏。”在他眼里,许多呼天抢地不过是政治秀场的配料。他不想把人生最后的告别做成仪式加工厂。

其二,尝遍人情冷暖后,他对“情感节制”近乎苛刻。晋军溃散时,不少部下自尽,也有换旗易辙的。他晚年常嘟囔:“人心可畏,可叹,可笑。”哭声在他看来是外化的情感洪水,他要的却是沉默中的克制。
其三,他正在推行“中的哲学”——凡事求中和平正。悲声若溢,情绪便失衡。故而遗嘱里点名让众人每日诵《补心录》:以读书的平和代替情绪宣泄,用理性把送行者的心安抚。

一九六〇年五月初,他突然腹泻浮肿。23日下午,病榻上的他忽然精神一振,招手唤贾景德上山,两人从军旅旧事聊到阴阳生死。贾劝他安心医治,他摆手:“药能治身,心病须我自医。”傍晚时分,他再次昏沉,深夜送入台北荣总,抢救无效,寿终七十七岁。
身后事没闹大阵仗。因事先交代,一切从简。从阳明山抬棺下山时,只听见鸟声。守灵期间,部下与遗孀徐竹青仍发生财产纷争。阎锡山生前说过“财产是工具”,可活人总有各自打算。打官司的消息传到报纸上,读者摇头:昔日一省之主,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私产漩涡。子女大都散居海外,除四子阎志敏返台外,其余因机票与各自生计缺席吊唁,连荒山旧坟也没走一趟。这份“飞鸟投林”式的散局,为阎氏家族的台湾章节画下句点。
要评阎锡山的一生,不少史家用“介于北洋与国府之间的灰色人物”来定位。他当过山西王,也当过“行政院长”,既自负又务实,有时冷酷,有时节制。可无论褒贬,最后那条“不可放声而哭”的遗言,道出一种超然:在漫长的政治洪流里,他见惯哭声被利用,更看透情感掺杂利益。死亡面前,他索性把哭声删掉,让自己退出舞台时只留静默。不可否认,这份克制既透露出“军阀式骄傲”,也带着晚年思辨后的清醒。

将视线放到六十余年前的台北,山雾翻滚,寂静的菁山草庐里,灵柩四周无嚎啕。这种冷静的送别方式,也许正是阎锡山对自己半生功过的一声叹息:哭不如思,哀不如省。当年勒石的“功业尽处,剩一个身心学问可守”八个字,如今读来,别有讽刺,又有几分超然。对于看惯战争、政争、金钱角力的七十七岁老人来说,最大的体面不是万人空巷的哭声,而是不再让他人替自己表演悲伤。
金斧子配资-金斧子配资官网-郑州股票配资网-炒股配资交流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